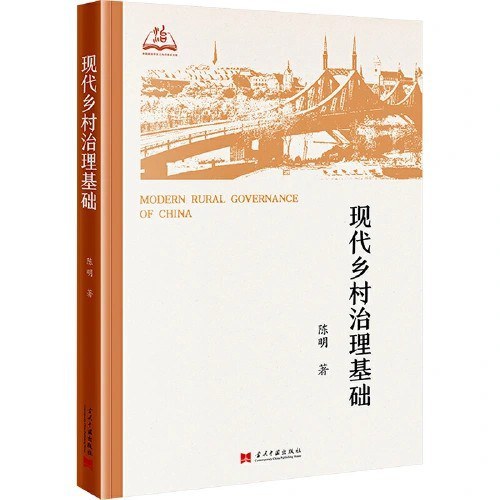
《现代乡村治理基础》,陈明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25年1月版
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是国人近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中国乡村早已不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与经济场域,而成为一个日益开放、分化、不断重构的传统—现代复合体。面对这样一个复合的乡村形态,如何去实现乡村现代化并真正赋予它以现代性的秩序含义,是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传统上,人们通常将乡村治理理解为一个治理体制或治理模式问题,如果沿着这个路向探寻,那么当治理体制规定下来之后,真正可资研究的问题其实也就不多了。这也是过去多年中乡村治理研究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治理追求的是特定的秩序,而秩序本质上并非单纯由体制规定的,而是由深层的社会经济结构规定的,这就给了我们从学理上探寻秩序来源的广阔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陈明的新著《现代乡村治理基础》所做的即是这样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乡村治理的基础秩序
该书认为,乡村治理并非一个单纯的治理体制或治理模式问题,而是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以建构乡村秩序的过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在乡村社会塑造一套与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个前提性的设定将乡村治理研究引入了现代化视域当中,重新勘定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空条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后一步”。当我们谈论“农业现代化”时,往往预设它会比较顺畅地过渡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正如该书所示,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交叠界面”最容易发生断裂,现实中很多国家和地区城乡转型的失败恰恰发生在这一过渡阶段。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虽然可以带动农业机械化、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但这些成就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延伸至农村的整体发展。无论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还是乡村自身的社会结构与治理形态,常常在这个“交叠界面”遭遇瓶颈与风险。
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体制存量,任何一个国家传统乡村的现代转型都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问题。该书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乡村治理的基础秩序”这一学术命题,并结合中国实际,将通常意义的乡村治理研究转化为治理活动与农民形态、产权制度和空间布局等基础因素间互动秩序的分析,通过这样一个逻辑大循环有效拓展了乡村治理问题的分析空间。
专业农户:乡村秩序演进的内生动力
传统上,人们在分析乡村秩序问题时更加注重制度设计或乡土文化,却容易忽视农民内部的分化。该书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形态的演进脉络——从建国之初的革命农民,到集体化时期的公社农民,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农民和近年来日渐崛起的专业农户,农民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度分化。
专业农户凭借更强的市场化经营能力和更合理的要素整合方式,已逐步成长为乡村发展的内生性推动力量。但由此带来的村庄内部社会阶层的重构、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碰撞,也使乡村治理面临的局面愈加复杂。随着城乡人口布局变动,乡村治理活动直接覆盖的人口数量已经大幅减少,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乡村社会中的群体张力会减弱,乡村治理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应该是不断降低的;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精英逐步被专业农户这一新兴精英群体所替代,专业农户与留守小农户之间又会形成新的合作与对冲关系,这又给乡村治理活动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如何在产业发展、社区公平、社群合作之间找到新的均衡点,是该书在分析中所提出的一个极具价值的启示性议题。
构建开放性的土地产权秩序
在以土地为根基的乡村社会中,土地产权制度对于乡村秩序的建构至关重要。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都经过了工业文明的洗礼,但真正能够实现土地制度现代转型的国家并不多见。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殊之处在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交错,并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地分离、土地流转、宅基地空置、专业农户兴起等错综复杂的演变。其实,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与时俱进的,过去40年中改革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根据土地专属社会价值和技术边界的移动不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从而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配。
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个认识困境是很多人将土地集体所有制简单等同于“村社总有制”,实际后者只是在传统时代的德国、日本等国局地存在过,从来也不是中华文明的制度传统。该书通过全面深刻的理论分析揭开了这一制度迷雾,强调了土地制度在实际运作中的多元形态。
该书分析认为,要解决产权封闭带来的各种管理和发展难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的框架内探索更具“开放性”的产权秩序,比如重新界定集体成员资格、提供退出与再联合机制等,既尊重公有制原则,也兼容农地、宅基地灵活运用,为乡村振兴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打造更具弹性的制度平台。
空间布局优化破解“末梢治理”之困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推进,乡村人口与产业加速向城市集聚,越来越多的村庄陷入空心化、老龄化和公共服务塌陷的困局。该书认为,面对城乡形态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进程,当务之急是通过空间单元与治理单元的适应性重组,来匹配现代经济社会的分工要求。
书中的不少案例都呈现出类似的思考:其中既包括山东“合村并居”、江苏“相对集中居住”、西部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移民搬迁等硬性的空间布局调整措施,也包括区划调整、跨区域行政等弹性的空间跃迁方式。这些做法的一个共同含义都在于弥合“末梢治理”或“碎片治理”的局限,为正在高速分化与专业化的中国乡村社会提供更加顺畅的管理和服务。
要注意的是,空间重组绝非纯粹的技术问题,也涉及基层政治利益的重新配置,操作难度与成效往往因地而异。书中介绍了日本的市町村合并、广域行政等经验,提醒我们必须尊重地方差异以及公众需求的内在演变,避免“一刀切”。
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单向度的“农业变革”,还包括经济、社会、制度和公共服务的整体升级。若要突破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过渡的“交叠界面”的瓶颈,就必须回到现代乡村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治理之匙。农民形态的分化、产权制度的开放、空间布局的调整、分工秩序的深化,这些相互交织并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基础秩序。该书中关于乡村治理基础秩序的讨论,既立足宏观视野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结构性变动,又直面村庄与农民的日常场景,呈现了当代乡村治理或隐或现的张力、难题与前景。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